《給孩子的人生先修班》:科普第一步,孩子怕蟲嗎
妹妹問我,
為什么帶孩子總是有這么大的耐力和堅持?
為什么我總是會想那么多?
親愛的妹妹,
我必須要想得多、看得遠,
養育她們過今天,為的是成熟獨立的明天,
為的是她們以后擁有堅強、懂事、高尚的靈魂,
而我做的,永遠都不夠。
女兒生出來懷抱在胸前哺乳的時候,在打造教養生活的藍圖時,我便悄悄決定,一定不要讓她們因為性別的關系,而失去了在大自然享受與各式蟲子對話或嬉戲的樂趣。
我相信讓孩子感受生命的可貴或詩情,透過昆蟲的觀察,可以得到等量的透視,而這權利是不分男女的,女兒身,也可以在大自然的稀微透徹光線里,與蟲翻滾。珍古德不就是在非洲大地的黑猩猩凝視里,開展出她寬闊慷慨、受人敬重的此生么?
你是個怕蟲子、看到蟲會忍不住起雞皮疙瘩或驚叫的人嗎?
關于蟲子的怕或不怕,我個人的心境毋寧是有一些轉折的。
記得在我許多童年熾夏、無所事事的放學午后,我和玩伴們用西瓜皮誘引貪愛水果汁液的金龜子,小小一片西瓜皮有時候可以擠入十幾只漂亮壯碩的蟲子啊!我用一條細線綁在金龜子的腿上,牽著它迎風飛,或是把它放在我的手掌心,觀察它強健有勁的腿和薄透迷離的翅膀。我細細端詳,每天看了又看,只為我有大把大把孤獨的、沒被大人安排的時光。
當然,每天的最后,我會讓這些蟲子自由飛返到樹林里它們的來時路。
盡管當時沒有什么人告訴我關于生命萬物的尊重與憐惜,但因為我自己很喜愛這些午后蟲子的陪伴,所以也就油然生了“昆蟲也該受人類自由、平等、博愛的對待”的念頭。這就是生活體驗所給予兒童的力量吧!有時候,其影響更超脫于書本文字之上。
上了國中以后,不知怎地,經常看到女同學們被毛毛蟲嚇得驚聲尖叫、花容失色、抱頭鼠竄,我納悶:這不過三公分大的蠕動生物,為何卻讓一百六十公分高的巨大人類,如此害怕失措呢?可以輕易摧毀它們生命的,是我們人類本身呢,而這些微小的蟲子根本奈不了我們何,所以,該尖叫竄逃的,理應是蟲子而不是我們啊。
但為了不想在同儕之間顯得太古怪,漸漸地,我也開始被同化為“昆蟲好惡心恐怖喲”,仿佛女性看到世間昆蟲就應顯現出一股嬌與懼,才是一種“性別正確”。自此我和大部分的女生一樣,再也不曾把蟲子放在手心上,對望、端詳、贊嘆了。
當了母親之后,理解到“全人教育”是給孩子最適切最溫柔的生活方式。坐月子時重讀梭羅的《湖濱散記》,他經典描述了大自然帶給生命與靈魂的潤澤和靈感。我合上書本,轉頭很篤定地對丈夫說,今后,我們一起努力讓我們的孩子,在科普和生命教育上不要缺席吧。
下了這樣的決定以后,盡管Milla和Nana的身軀發展非常女性化地纖細瘦長,但從幼兒園起,經常與我們一起漫步山林的原野生活,逐漸發酵出姊妹倆對昆蟲生命的好奇與關愛。即至入小學,即使同班女生一看見蜘蛛爬或蜜蜂飛就高聲尖叫,也無損于她們對自然學科的興趣發展。
在Nana的眼里,恐龍意味著美好洪荒年代的代表性族群;黃口攀蜥的柔和霧面色彩,則是上帝最厲害的調色盤。觀察或了解這些生物,是沒有性別之分的。
我想,這是因為我經常收拾起內心的那一丁點兒恐懼,并不時面露贊許、欣喜,鼓起勇氣陪Nana四處看蟲、撿蟲而得來的。
今天中午放學在家的巷口,便看到一只手掌大的蟾蜍死于輪下被車壓扁的尸體(女兒告訴我這尸體上還看得到疣,所以是蟾蜍,不是蛙。)。死了是死了,但因為不忍心見它在烈日下繼續被踐踏,希望它死后至少能夠好好地上天堂,Milla和Nana于是撿拾起路邊的樹枝,合力把這只身體已干癟、臟腑已外露的動物,挪搬到草叢的泥土堆里。
兩個女兒小心翼翼地確認這大蟾蜍尸體已安然在芬芳的草泥上受掩蓋,才放心地往家的方向繼續邁進。這何嘗不是學校自然教室的延伸呢?不必去坊間補習做實驗,活生生的自然課,就在馬路邊、巷子口的小小生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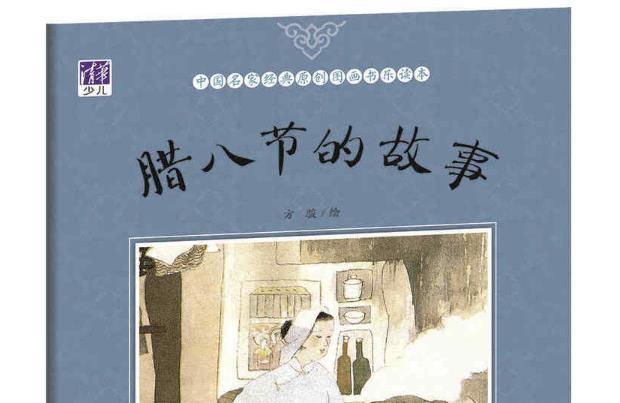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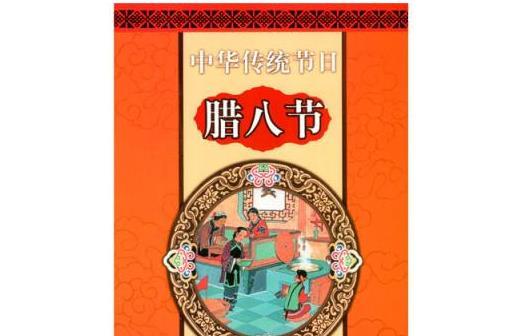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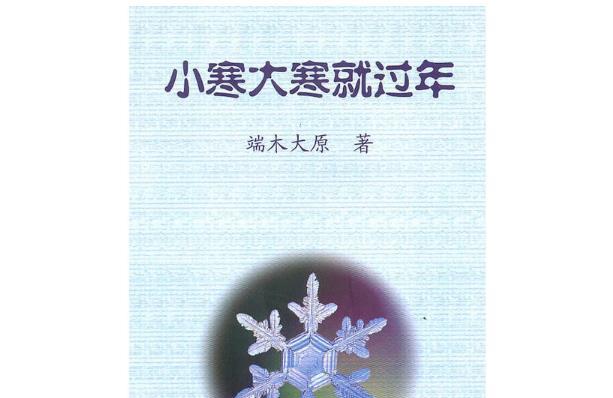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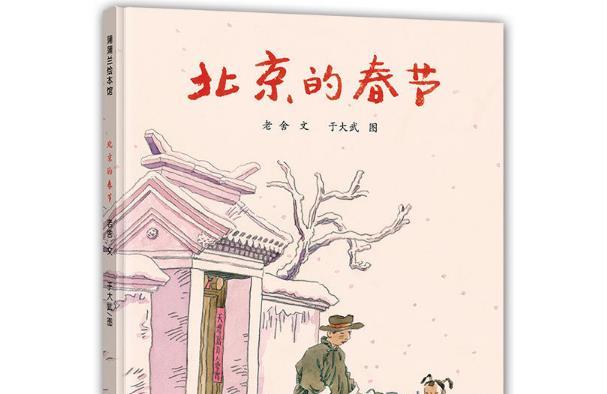





還沒有人評論哦,趕緊搶一個沙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