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銀島》黑狗的出現(xiàn)與消失(二)
那年冬天特別冷,父親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店里所有的活都落到了我和母親的肩上。
在正月里一個(gè)寒冷的早晨,太陽剛剛爬上山頂。這天,船長起得比平時(shí)都早,他夾著望遠(yuǎn)鏡向海邊走去,一柄水手彎刀在腰間晃蕩著。
母親當(dāng)時(shí)正在樓上照顧父親,我在樓下張羅船長回來要吃的早餐。忽然,客廳的門開了,一個(gè)我從未見過的人走了進(jìn)來,這個(gè)人又白又胖,左手缺了兩個(gè)手指,腰上也帶著一柄水手彎刀。這個(gè)人在一張桌子旁坐了下來,作了個(gè)手勢要我過去。
“孩子,過來,”他說,“桌上的早餐是不是為我的朋友比爾準(zhǔn)備的啊?”
我回答說,我不知道他的朋友比爾是誰,早餐是為住在我們店里的一位客人準(zhǔn)備的,我們都管這客人叫船長。
“是啊,”他說,“我這朋友比爾好像也被人稱作船長呢。你這位船長的右邊臉頰上有個(gè)刀疤,是不是?——啊,對了,我找的就是他!”
我告訴他船長出去散步了。
于是這陌生人便老是在店門口旁轉(zhuǎn)悠,還不時(shí)向外張望,活像一只貓?jiān)谑刂鲜蟆?/p>
沒過多久,船長遠(yuǎn)遠(yuǎn)地朝旅店走來了。陌生人立刻把我拉到他身后,一齊躲進(jìn)了門背,我當(dāng)時(shí)緊張極了。陌生人把彎刀從刀鞘里往外拔了拔。
船長邁著大步走了進(jìn)來,沒有向左右兩邊看上一眼,就徑直走到了為他準(zhǔn)備好的餐桌旁。
“比爾。”陌生人叫了一聲。
船長猛地轉(zhuǎn)過身來,臉色頓時(shí)鐵青,好像看到了惡魔似的。他倒吸了一口涼氣,說了一聲:“黑狗!”
“正是你同一條船上的老伙計(jì)——黑狗!” 陌生人稍稍松了口氣說道。
黑狗在船長的早餐桌旁坐了下來。等我端上了朗姆酒,黑狗便要我走開,并讓我把門開著。
過了一會兒,客廳里突然爆發(fā)出一陣可怕的咒罵聲,同時(shí)還夾雜著其他響聲——椅子和桌子被掀翻的碰撞聲,鋼刀的乒乓聲,再接著便是什么人發(fā)出的痛苦的嚎叫聲。
我趕緊跑進(jìn)來,只見黑狗肩上血流如注,沒命地往外跑,船長在后面窮追不舍,兩個(gè)人的手中都握著出鞘的彎刀。追到門口時(shí),船長朝黑狗使勁砍去,可是,“本鮑將軍”招牌擋住了他的彎刀。
黑狗趁機(jī)飛快地逃走了,而船長卻像中了邪一樣站在那里,死死地盯著招牌。他把眼睛揉了好幾下,這才回到屋里。
“吉姆,”他喊道,“拿朗姆酒來。”
“朗姆酒。”他自言自語地說,“我必須離開這里。朗姆酒!朗姆酒!”
我慌慌張張地跑進(jìn)里面拿酒,突然聽到客廳里傳來一聲巨響,跑出來看時(shí),船長已經(jīng)直挺挺地躺在了地板上。響聲也驚動了樓上的母親,她跑下樓來。
我和母親都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碰巧這時(shí)李甫西大夫推門進(jìn)來,他是來給我父親看病的。
大夫說船長根本沒有受傷,而是中風(fēng)了。然后,大夫讓我母親上樓去照顧父親,又讓我拿了一個(gè)臉盆來。
“吉姆,”大夫問,“你怕見到血嗎?”
“不怕,先生。”我說。
“那么,”大夫說,“你端著這個(gè)盆子。”他邊說邊拿起一把手術(shù)刀,割開了船長的靜脈。
流了許多血后,船長終于睜開了眼睛,迷迷糊糊地看了看四周。突然,他嚷道:“黑狗在哪兒?”
“這里沒有什么黑狗,”大夫說,“只有你仰面朝天地躺在這里。你放肆地喝酒,結(jié)果正如我說的那樣,中風(fēng)了。盡管我萬分不愿意,可剛剛我還是把你從墳?zāi)估锢嘶貋怼B犞绻悴悔s快把酒戒掉,你會沒命的!”
船長不高興地皺起了眉頭。
我和大夫兩個(gè)人費(fèi)了很大的勁才把他扶上樓,讓他躺在床上。然后,我跟著大夫一起看我父親去了。
相關(guān)文章
更多>網(wǎng)友評論
熱門關(guān)注
更多>- 懷孕 保養(yǎng)子宮健康,聰明女人都這么做|孕期睡眠|上環(huán)|產(chǎn)褥感染|刮宮|習(xí)慣性流產(chǎn)|習(xí)慣性流產(chǎn)|保胎
- 育兒 囟門|螨蟲|一歲寶寶身高體重表|寶寶受涼|完達(dá)山奶粉|寶寶肛門周圍紅|換牙時(shí)間表|兒童生長發(fā)育
- 早教 孩子叛逆期|爛布片|沒有畫的畫冊|薊的遭遇|民歌的鳥兒|區(qū)別|各得其所|風(fēng)車
- 營養(yǎng)美食 大蒜|杏仁|紅棗|檳榔|百合|山楂|洋蔥|花生
- 保健養(yǎng)生 乳房按摩有用嗎|婦科檢查包括哪些項(xiàng)目|爬山減肥|手腳冰涼|白醋泡腳的好處|手上長小水泡|私處洗液|手掌脫皮
- 生活用品 嬰兒車品牌|兒童積木|驅(qū)蚊手環(huán)|電子驅(qū)蚊器|兒童防曬霜|牙膠|嬰兒指甲鉗|孕婦吃魚肝油對寶寶好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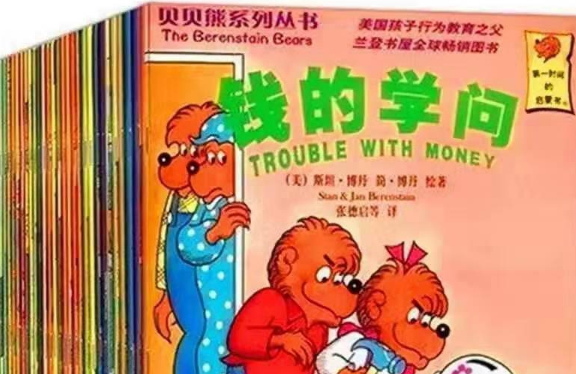









還沒有人評論哦,趕緊搶一個(gè)沙發(f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