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好看嗎?口碑票房都達(dá)不到預(yù)期效果
《白鹿原》幾經(jīng)波折,終于上映了。究竟這部《白鹿原》是不是讀者心目中的白鹿原呢,這部《白鹿原》值不值得期待呢?據(jù)了解,這部《白鹿原》既沒有預(yù)期的口碑,也沒有預(yù)期的票房,這部156分鐘的公映版只保留了田小娥這條線索,讓觀眾實(shí)在摸不著頭腦。
籌備9年、拍攝3年,根據(jù)陳忠實(shí)同名小說改編,由段奕宏、張雨綺、張豐毅等主演的影片《白鹿原》“歷經(jīng)磨難”,近日終于上映。就目前的反饋情況看,這部吊足觀眾胃口、展示了導(dǎo)演王全安雄心大志的“史詩(shī)作品”并未收獲預(yù)期的口碑,批評(píng)和惋惜之聲不在少數(shù)。
有的電影讓你從一開始就抱著純粹消遣的態(tài)度,有的電影則讓你懷著一顆等待被征服的心,以致一旦在細(xì)節(jié)推敲上略有差池,便會(huì)失望如潮,《白鹿原》屬于后者。

洋洋灑灑50多萬(wàn)字的長(zhǎng)篇小說《白鹿原》獲得了第四屆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中國(guó)電影便開始了對(duì)《白鹿原》的關(guān)注,第四代導(dǎo)演吳天明,第五代導(dǎo)演張藝謀、陳凱歌都曾努力想把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但業(yè)界有句話,“越好的小說越難改”——正因?yàn)椤栋茁乖愤@條“船”太大,人物、道具、場(chǎng)景環(huán)環(huán)相扣,所以很難改編。接過舵盤的王全安首先要做的是“舍棄”和“重塑”,用最精煉的電影語(yǔ)言放大原著中最深刻、最感人的因素。
不過,我們無(wú)緣看到被評(píng)價(jià)為“劃時(shí)代”的220分鐘初剪版,但就目前影院放映的156分鐘版本《白鹿原》來(lái)說,不熟悉原著的觀眾普遍感覺情節(jié)跳躍,有些虎頭蛇尾;熟悉原著者可能會(huì)覺得寡淡無(wú)味,只看了半部《白鹿原》——從體量上看,1993年版《白鹿原》共680頁(yè),電影中留到最后的田小娥在第 340頁(yè)就死于梭標(biāo)下;而就小說所表達(dá)的主題來(lái)說,無(wú)論從深度還是廣度,電影甚至都難及原著的一半。
影片后半段,敘事節(jié)奏明顯加快,畫面因?yàn)榧糨嫸霈F(xiàn)跳躍感。令人垂涎的油潑面、慷慨激昂的秦腔、一再被表達(dá)的麥浪……王全安把這些符號(hào)化的東西做足了,讓人聯(lián)想起30年前的張藝謀。但問題是,搭好了戲臺(tái),戲卻沒能唱響——一段、兩段,點(diǎn)到即止,欲說還休。白嘉軒的背景沒有交代清楚,鹿兆鵬的革命顯得非常匆忙,長(zhǎng)工鹿三的瘋狂缺少必要鋪墊……隨著悲劇的氛圍越來(lái)越重,觀眾期待的高潮卻始終沒有出現(xiàn),寒來(lái)暑往、串接轉(zhuǎn)場(chǎng),導(dǎo)演的鏡頭似乎始終沒有離開過田小娥。就這樣,“白鹿原”從一個(gè)廣袤的地理概念被簡(jiǎn)化成了一間破窯、一席炕和一個(gè)女人,盡管故事性和戲劇張力得到了強(qiáng)化,卻忽略了原著中“新與舊”、 “家與國(guó)”的沖突,觀眾捏合眼前的碎片,看不到一個(gè)時(shí)代波瀾壯闊的興衰沉浮。
20多年前,陳忠實(shí)用手中的筆為白鹿原賦予了靈魂,那只在雪地里奔跑的神鹿和它所代表的神圣純凈的世界,就是白鹿原人的信仰所在。現(xiàn)在,我們可以對(duì)這部已難覓神鹿蹤跡的改編電影挑刺,但不能否認(rèn),這部有著美得不能言說的土地、燃燒的夕陽(yáng)、金黃的麥田、圖騰般兀立的牌坊的文藝片,還是會(huì)和那些質(zhì)地相似的電影一起,比如《活著》、《黃土地》等,在觀眾心里留下些什么。
相關(guān)文章
更多>網(wǎng)友評(píng)論
熱門關(guān)注
更多>- 懷孕 保養(yǎng)子宮健康,聰明女人都這么做|孕期睡眠|上環(huán)|產(chǎn)褥感染|刮宮|習(xí)慣性流產(chǎn)|習(xí)慣性流產(chǎn)|保胎
- 育兒 囟門|螨蟲|一歲寶寶身高體重表|寶寶受涼|完達(dá)山奶粉|寶寶肛門周圍紅|換牙時(shí)間表|兒童生長(zhǎng)發(fā)育
- 早教 孩子叛逆期|爛布片|沒有畫的畫冊(cè)|薊的遭遇|民歌的鳥兒|區(qū)別|各得其所|風(fēng)車
- 營(yíng)養(yǎng)美食 大蒜|杏仁|紅棗|檳榔|百合|山楂|洋蔥|花生
- 保健養(yǎng)生 乳房按摩有用嗎|婦科檢查包括哪些項(xiàng)目|爬山減肥|手腳冰涼|白醋泡腳的好處|手上長(zhǎng)小水泡|私處洗液|手掌脫皮
- 生活用品 嬰兒車品牌|兒童積木|驅(qū)蚊手環(huán)|電子驅(qū)蚊器|兒童防曬霜|牙膠|嬰兒指甲鉗|孕婦吃魚肝油對(duì)寶寶好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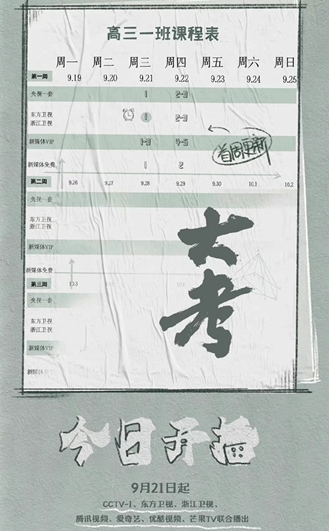





還沒有人評(píng)論哦,趕緊搶一個(gè)沙發(f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