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孩子人生的先修班》:間接,婉轉,幸福的力量
在教導孩子的過程中,有時候我們的說話技巧決定了孩子的受教程度。間接、婉轉的說話藝術,更具有說服力。我們一起看看作者是如何通過一系列的例子表達這方面的說話藝術的。
間接、婉轉,更具有勸說的力量。
與其對孩子把話說得太粗糙,
不如多想想,真誠細致的話的極致美。
把話說到孩子的心坎里,
讓孩子享受到生存的快樂、看到自我的權能,
讓孩子們學習在心靈上自我安頓,
如此,他怎么能不感到自己是這般地受愛寵與幸福呢!
我幾乎不對我的孩子刻意說,你看,你有多幸福,你有多好命,你應該要好好珍惜你的生活,等等,因為我認為這樣略帶強迫性的語句,不僅直擊不到孩子天真的心里,并且,還讓人感到一股被隱隱責備的侵犯。孩子認為自己幸不幸福,并不是爸媽說了就算,他們心底是否深刻地認同到自己被幸福地對待與愛寵,才具有意義。
因此,當我們好幾次在大馬路上的驕陽毒日或寒風冷雨中,看見年邁的老者與幼童,吃力地推著滿載資源回收物的鐵板車,在川流不息的車陣中緩慢地匍匐前進時,我不會轉過頭對緊握我雙手的 Nana 說:“你看看,你不用為生活發愁,放學不必像這個小朋友一樣,還得去幫忙做資源回收,你可知你有多幸福!”
他人的生活辛苦,不應當是我教養孩子的比較教材。孩子親眼目擊到這底層生活的景象,必然已有慈憫之心,慈憫本身已是珍貴溫潤的美德,此時我若突然冒出“可見你有多幸福”的姿態,氛圍就整個反轉到一個八股的情境,不僅欠缺感動孩子的力量,也毀壞了他其實正默默觀察著的震撼。
有一次放學后,我們直接到馬偕醫院看病,就診結束時刻已近黃昏,在密閉的大醫院里熬了好幾個小時走出來,終于呼吸到新鮮流動的空氣,爽颯流離的天光使我們振奮些許。Milla和 Nana 各自背著大書包、便當袋和美勞袋,我也背著我的沉沉老筆電,母女三人頗疲累了。Nana 嘟著嘴說:“媽咪,我好餓啊!”但我們仍然互相打氣著,五十分鐘過后的公交車,就可以把我們帶回貓咪在等待著的家。
此時,等候紅綠燈的我們,看到一位八十歲左右的老者,推著厚重到幾乎要翻覆的鐵板車,卡在大馬路中間動彈不得,身邊的小孫子漲紅著臉、氣喘吁吁,有一刻我真的以為他們永遠都過不了這個路口。喧囂繁華的中山北路,高貴氣派的精品店林立,不耐煩的喇叭聲此起又彼落,更顯得這兩位老小的吃力勞動,在林蔭大道下,是如此地滄桑不忍。我輕嘆低語著:這世上就是有人要這么受苦嗎?
約莫過了三十秒,我們母女三人共同決定,何不就把筆電和書包擱置在樹下,到大馬路上幫他們推車,以解決這卡在半路、難以進退、即將淹覆的窘境呢?
這推車的報紙和寶特瓶重量,很是驚人! Milla 和 Nana 協同陌生的老者小孩,把鐵板車緩步推過穿梭的如水車流,再回頭背起自己的書包,擠上巔峰時間的沙丁魚公交車,抿著嘴唇默默無言,想必正體會自己的生活,原來如此溫暖安定吧。
此時,我要自己千萬別說出“這下子你知道你有多幸福了!”這樣徒具形式的話,我不想要把別人生活他方的辛苦,當作我教養的體裁,我也不要我的孩子厭倦這種流于形式的叨絮。
更多的時候,實踐與行動,便千萬雷霆萬鈞于語言了。
我也不愛在餐桌上對孩子說,非洲小孩很窮很可憐都沒飯吃了,你這么幸福,還不懂得惜福,還不快快把飯吃完!
因為這樣的話語,除了責備之意,聽不到任何的慈憫或積極性,孩子聽多了這隱含負面感的言詞,久而久之,甚至對非洲兒童的處境更無感。因為被爸媽無意、無心地濫用了。
所以,我嘗試著用另外一種角度,與孩子溝通第三世界的問題。大抵我會談世界展望會這些年在非洲做了哪些慈善義舉;微軟富豪比爾·蓋茨,捐出大筆金錢研發疫苗來救助這些落后國家的生命;或者,臺灣的農耕隊在非洲貧瘠的土地上,慷慨捐輸了我們數十年來自身累積的知識與技術,給非洲農民帶來實質生活上的改善與希望。每一個孱弱的生命,都是我們世界公民的責任。
當我在為孩子述說這種種來自富裕或已開發國家,所給予第三世界的積極性援助,配合那么多國際新聞的真實感人攝影,其實已在無形中,訴說不盡她們的童年小日子,原來這般靜定富足。
間接、婉轉,更具有勸說的力量。與其對孩子把話說得太粗糙,不如多想想,真誠細致的話的極致美。
那么,我的孩子們,是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幸福的?是誰讓她們放學后在餐桌上,對我感恩言謝的?是孩子們同學的無心之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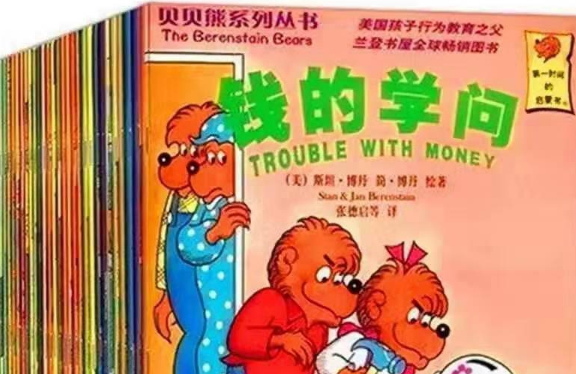









還沒有人評論哦,趕緊搶一個沙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