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魯迅手抄報圖片簡單
走進魯迅手抄報圖片簡單:小說特色
魯迅的小說選材獨特,在題材的選擇上,魯迅對古典文學中只選取“勇將策士,俠盜贓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來則有妓女嫖客,無賴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為人生”的啟蒙主義式的創(chuàng)作目的,開創(chuàng)了“表現(xiàn)農(nóng)民與知識分子”兩大現(xiàn)代文學的主要題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魯迅在處理這些題材時又具有極其獨特的眼光。在觀察和表現(xiàn)自己的主人公時,他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即始終關(guān)注著“病態(tài)社會”里知識分子和農(nóng)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鄉(xiāng)》中,最震動人心的不是閏土后來的貧苦,而是他一聲“老爺”所顯示的心靈的麻木。對知識分子題材的開掘,又著眼于他們的精神創(chuàng)傷和危機,如《在酒樓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獨戰(zhàn)多數(shù)的英雄擺脫不了孤獨的命運,在強大的封建傳統(tǒng)壓力下又回到原點,在頹唐中消耗著自己的生命。魯迅的這些改革在《吶喊》和《彷徨》中就演化為“看/與被看”與“歸鄉(xiāng)”兩大小說情節(jié)、結(jié)構(gòu)模式。小說《示眾》中所有人的動作只有“看”,關(guān)系也只有“看”與“被看”,由此形成了“看”與“被看”的二元對立,這種對立在《狂人日記》、《孔乙己》、《祝福》等小說中都有展現(xiàn)。而在“歸鄉(xiāng)”模式中魯迅不僅講述他人的故事也講述自己的故事,兩者互相滲透,影響,構(gòu)成一個復調(diào),如在《祝福》中,講“我”、“祥林嫂”與“魯鎮(zhèn)”的三重關(guān)系,這個關(guān)系中既包含“我”與“魯鎮(zhèn)”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與魯鎮(zhèn)的故事,然而讀者往往忽視前者,前者講一個“永遠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講一個封建社會吃人的故事。兩個故事相串聯(lián),以祥林嫂的問題拷問“我”的靈魂,從而揭示“我”與魯鎮(zhèn)傳統(tǒng)精神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類似這種模式的小說還有《故鄉(xiāng)》、《孤獨者》和《在酒樓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魯迅一直在探索主體滲入小說的形式。《在酒樓上》和《孤獨者》中,小說的敘述者“我”與小說人物是“自我”的兩個不同側(cè)面或內(nèi)心矛盾的兩個側(cè)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靈魂的對話與相互駁難的性質(zhì)。另一方面,魯迅也在追求表達的含蓄、節(jié)制、以及簡約、凝練的語言風格。他曾說“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求能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肯什么陪襯也沒有。”對此他在介紹寫小說經(jīng)驗時也說“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xiàn)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這也說明魯迅在描寫人物時著重人物的精神風貌,在描寫中非常注重農(nóng)民的藝術(shù)趣味。魯迅研究了農(nóng)民喜歡的舊戲和年畫的藝術(shù)特點,并運用在自己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使他的小說顯示了濃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廣泛借鑒了詩歌、散文、音樂、美術(shù),以至戲劇的藝術(shù)經(jīng)驗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并且試圖融為一爐,于是出現(xiàn)了“詩化小說”(《傷逝》、《社戲》等)、散文體小說(《兔和貓》、《鴨的喜劇》等),以至“戲劇體小說”(《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魯迅的創(chuàng)作精力主要放在雜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記小說的創(chuàng)作,并貢獻了他最后的創(chuàng)新之作《故事新編》。這部小說集依舊展現(xiàn)了魯迅不羈的想象力與強大的創(chuàng)造力:對在《吶喊》和《彷徨》中創(chuàng)建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創(chuàng)作規(guī)范進行新的沖擊,尋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編》中,魯迅有意識的打破了時空界限,采取“古今雜糅”的手法:小說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歷史記載外,還創(chuàng)造了一些次要的戲劇性的穿插人物,在他們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現(xiàn)代語言,情節(jié)和細節(jié)。用現(xiàn)代語言自由發(fā)揮,以“油滑”的姿態(tài)對對現(xiàn)實進行嘲諷和揭露。同時在許多篇什中都存在著“莊嚴”和“荒誕”兩種色彩與語調(diào)旋律,相互補充,滲透于消解。例如《補天》中,女媧造人時的宏大與瑰麗令人向往,而結(jié)尾,后人打著“造人、補天”的旗幟在死尸的肚皮上安營扎寨又顯得極其荒誕,這種荒誕將前文的偉大感消失殆盡,并轉(zhuǎn)化為一種歷史的悲涼。

走進魯迅手抄報圖片簡單:魯迅的雜文特色
魯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別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與心血于雜文創(chuàng)作中。他的雜文極具批判性,魯迅曾把雜文分為“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強調(diào)的正是雜文的“批評(批判)”內(nèi)涵與功能。順次翻開魯迅生前出版的14本雜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論戰(zhàn),反擊……的思想文化斗爭的編年史:從《熱風》開始的對封建禮教、舊傳統(tǒng)的批判,與復古派的論爭,一直延續(xù)到《且介亭雜文末編》對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專政的抗議,對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的“左傾”路線的反擊。魯迅雜文所顯示的這種“不克厥敵,戰(zhàn)則不止”的不屈精神,從根本上有違于中國文化與中國士大夫文化知識分子的“恕道”、“中庸”傳統(tǒng),集中的體現(xiàn)了魯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異質(zhì)性。
魯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評論,他把自己的批判鋒芒始終對準人,人的心理與靈魂:這是一種文學家的關(guān)照。正如魯迅自己說:“我的習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為關(guān)注的正是人們隱蔽的,甚至自身無法自覺意識的心理狀態(tài)。如雜文《論“他媽的”》,魯迅在國人習以為常的“國罵”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級、門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魯迅還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據(jù)此而寫出的一些雜文,例如《小雜感》:“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魯迅的雜文思維也是非規(guī)范化的,他常在常規(guī)思維路線之外,另辟蹊徑,別出心裁,就打開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學術(shù)隨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guān)系》中就以這種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樣的結(jié)論:嵇、阮對禮教的破壞只是表面現(xiàn)象,事實上卻是愛之過深的表現(xiàn)。魯迅雜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難以接受,還在于他的同樣違反“常規(guī)”的(聯(lián)想力)想象力,魯迅一方面將外觀形式上離異最遠似乎不可能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人和事連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發(fā)現(xiàn)“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夠發(fā)現(xiàn)和感受到歷史與現(xiàn)實的獨特聯(lián)系。在《小品文的危機》中“煙花女子,已經(jīng)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馬路上來”。這樣一端是高貴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在經(jīng)過魯迅的牽連下就達到了“神圣”的“戲謔化”,“高雅”的“惡俗化”。
“將具體的、個別的人與事排除個別性、具體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義懂得整體概括,并加以簡括的名稱,經(jīng)‘這一個’提升為‘這一類’的‘標本’,同時保留著形象、具體的特征,成為‘個’與‘類’的統(tǒng)一”這是魯迅在進行論戰(zhàn)時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魯迅生前的14本雜文集中塑造了許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兒狗”、“西崽”、“洋場惡少”、“革命工頭”等等。這些形象常是對某人一時一地的言行作為一種典型現(xiàn)象來加以解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從而提煉出的一種社會類型,這些形象具有超時空的意義,這也使得這種類型的“共名”與魯迅小說里的阿Q、祥林嫂一樣,具有長遠的藝術(shù)生命力。
與思想的天馬行空相適應(yīng),魯迅雜文的語言也是無拘無束而極富創(chuàng)造力的。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把漢語的表意、抒情功能發(fā)揮到了極致。在他的雜文中:或口語與文言句式夾雜;或排比、重復局勢的交叉運用;或長句與短句、陳述句與反問句的相互交錯,混合著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與氣勢,可謂“深情并茂”。如《記念劉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酣暢淋漓,氣勢可觀。而在另一方面,魯迅雜文的語言又是反規(guī)范的,他故意地破壞語法規(guī)則,違反常規(guī)用法,制造一種不和諧的“拗體”,以打破語言對思想的束縛,同時取得荒誕、奇峻的美學效果。比如他有時將含義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詞組織在一起,于不合邏輯中顯深刻:“有理的壓迫”、“跪著造反”、“在嫩苗上馳騁”等等。

相關(guān)文章
更多>網(wǎng)友評論
熱門關(guān)注
更多>- 懷孕 保養(yǎng)子宮健康,聰明女人都這么做|孕期睡眠|上環(huán)|產(chǎn)褥感染|刮宮|習慣性流產(chǎn)|習慣性流產(chǎn)|保胎
- 育兒 囟門|螨蟲|一歲寶寶身高體重表|寶寶受涼|完達山奶粉|寶寶肛門周圍紅|換牙時間表|兒童生長發(fā)育
- 早教 孩子叛逆期|爛布片|沒有畫的畫冊|薊的遭遇|民歌的鳥兒|區(qū)別|各得其所|風車
- 營養(yǎng)美食 大蒜|杏仁|紅棗|檳榔|百合|山楂|洋蔥|花生
- 保健養(yǎng)生 乳房按摩有用嗎|婦科檢查包括哪些項目|爬山減肥|手腳冰涼|白醋泡腳的好處|手上長小水泡|私處洗液|手掌脫皮
- 生活用品 嬰兒車品牌|兒童積木|驅(qū)蚊手環(huán)|電子驅(qū)蚊器|兒童防曬霜|牙膠|嬰兒指甲鉗|孕婦吃魚肝油對寶寶好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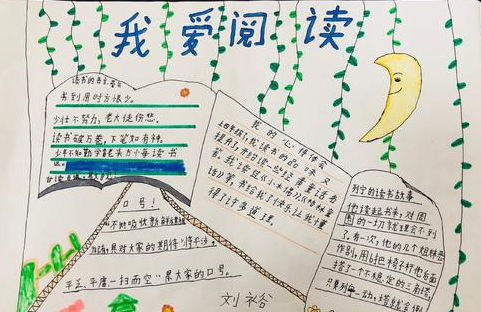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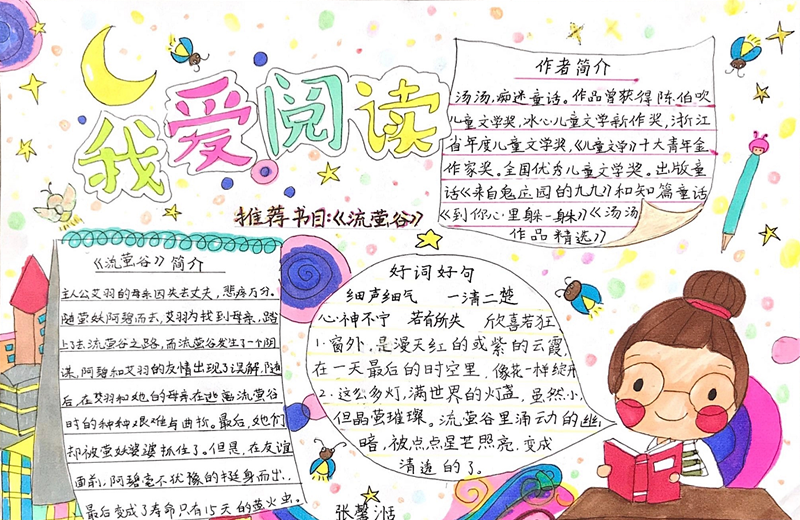


 11:52
11:52
 14:16
14:16
 17:54
17:54
 17:05
17:05
 10:43
10:43
 10:52
10:52











還沒有人評論哦,趕緊搶一個沙發(fā)吧!